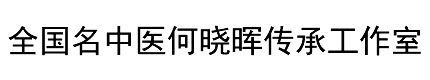本次主题为“肝郁化火证”。主讲人:江西中医药大学赖同学
概念:肝郁化火证是指由于肝气郁结日久,郁而化火内扰所表现的证候。
临床表现:主症:胸胁胀满灼痛,心烦易怒,口苦。症状:两胁胀闷灼痛,精神抑郁,胸闷喜叹息,心烦易怒;或胃脘灼热,嗳气吞酸;或有低热,口苦咽干,尿黄短,寐差多梦。 舌象:舌红,苔黄。 脉象:弦数。
辩证要点:本证以肝郁气滞证与内热证共见为审证要点。
成因:本证多为肝郁气滞证日久不解,郁而化热而成。
病机:本证的主要病机是肝气郁结,气郁化火。肝气失于疏泄,气机不畅,故两肋胀闷,胸闷喜叹息。情志失于调畅,则精神抑郁。热郁于内,灼于肝络则胁肋灼痛;横逆犯胃,灼于胃腑则胃脘灼热。气火内郁,不得宣泄,故心烦易怒,或有低热。热扰胃胆,气机上逆则嗳气,吞酸,口苦。热伤津液则咽干,尿黄短。舌红苔黄,脉弦数为郁热之象。
发展与转归:1.肝郁化火证进一步发展,气火上逆,而成为肝火炽盛证。 2.肝郁化火证日久必伤肝阴,致肝阴虚;阴不制阳,又可成为肝阳上亢证。3.热可煎熬津液为痰,气热痰三者交结为患,成为肝郁痰火证。
疾病范围:1.中医:本证常见于郁证、胁痛、胃痛、内伤发热等病证中。2.西医:本证主要见于神经官能症、抑郁性神经症、慢性胃炎、慢性肝炎、慢性胆囊炎、功能性发热、更年期综合症等疾病过程中。
类证鉴别:1.肝火炽盛证:同:均为肝郁发展而来,病机基本相似,均有明显热象。 异:肝火炽盛证的特点是火势炎上,热象主要在头面部,如头痛头晕、面红、目赤耳鸣、吐血衄血等;而本证头面部热象不明显,而表现为胁肋灼痛、胃脘灼热、心烦易怒、身有低热等,热势较缓。
2.肝郁气滞证:肝郁气滞证是肝郁化火证的病理基础,因为尚未化火,故热象不明显。
3.胃火证:肝郁化火证可以影响于胃,出现胃部灼热、吞酸、口干等,故应与胃火证鉴别。胃火证有消谷善饥、口臭、牙龈肿痛出血、便结等胃火炽盛的症状;而本证有明显的精神抑郁、胁肋胀闷、心烦易怒、口苦等肝经郁热症状。
治法:疏肝解郁清热
主方:丹栀逍遥散(丹皮、栀子、柴胡、白芍、当归、白术、茯苓、薄荷、炙甘草、生姜)
【功能】疏肝解郁,健脾和营,兼清郁热。
【主治】肝郁化火,潮热颧红,月经不调,少腹胀痛,经行乳胀,崩漏,带下。
【方解】柴胡疏肝解郁,当归、白芍养血柔肝。尤其当归之芳香可以行气,味甘可以缓急,更是肝郁血虚之要药。白术、茯苓健脾去湿,使运化有权,气血有源。炙甘草益气补中,缓肝之急,生姜,温胃和中,薄荷少许,助柴胡疏肝郁,又能透达肝经郁热。丹皮、栀子,清热泄火。如此配伍既补肝体,又助肝用,气血兼顾,肝脾并治,立法全面,用药周到,故为调和肝脾之名方。
加减:肝郁较甚者,加用香附、郁金;胁痛甚者,加川楝子、元胡索;失眠多梦者,加合欢皮、酸枣仁;低热者,加地骨皮、胡黄连、青蒿等。
治疗要点: 本证为郁火,“木郁达之”,故治疗宜疏达宣散,而不能径用苦寒直折其火,因寒主凝滞,愈清则火愈郁。必须配伍辛散疏达,甘滋润柔之品,以疏肝达郁、垄肝化断化火之机。
拓展:亢害承制与从肝论治失眠症
当今失眠症临床证候的主要特点是:精神亢奋者多,精神衰弱者少;中壮年人较多,老年人较少;精神情志因素合并其他躯体疾病或精神疾病者多,单纯体质因素先天不足,无其他夹杂病者少。因有承制则生化,亢而无制则病生。说明亢害现象是当今失眠症临床证候的主要表现,肝木偏旺是失眠症发病的主要病理基础。肝木过于亢盛,常易犯胃,临床上多见胃胀、嗳气频作,即所谓“胃不和则卧不安”。此谓胃病不寐,治宜平肝解郁、和胃降逆的方药,以加味柴胡龙牡汤,加蒲公英、佛手、苏梗、煅瓦楞子、生麦芽等。抑木则胃自和,和胃则木自达。可见,在五行运行中,要重视“制”在生化中的决定作用,只有五行相互制约,才能维持正常的生长和变化。 五行的制化现象,不是静止不变的,它随五行之间的盛衰盈虚不断变化,产生作用。肝木亢盛而侮肺金,致肺失清肃。如:感冒发热,余邪未清再加精神过劳,常患呛咳不已,夜寐不安,数月不愈,用一般宣肺化痰药无效,证属燥咳不寐,此谓肺病不寐,用平肝活血安神方,加百合、桑叶、银花、连翘、款冬花、桑白皮等清热润肺之剂。亢而承制,平其所复,扶其不胜,则呛咳自平。 又如中老年妇女患者,临床上常见夜不安寐、尿频、尿急。乃肝阳上亢,肾气不足,证属肝亢肾虚,此谓肾病不寐。治以平肝补肾安神,以柴胡、龙骨、牡蛎、天麻、钩藤为基本方,加菟丝子、金樱子、芡实、补骨脂之类。肝肾乙癸同源,肝平则肾气固,益肾则肝亦平。 肝木亢盛,心火上炎,母病及子。临床表现夜难入寐,胸闷心悸,心烦不安,证属肝亢犯心,此谓心病不寐。治以平肝或疏肝解郁、活血养心安神,以基本方加赤芍药、丹参、川芎、郁金、五味子、远志、灯芯等。抑木则心自安,心血和则木亦达。可见,脏腑病变,除按五行运气的一般规律“克其所胜”外,尚可见于殃及邻脏或侮其所不胜者。
名家医案
孙某,女,60岁。1994年1月4日初诊。 患者近日因情志不遂而心烦不宁,坐立不安,整夜不能入寐,白昼则体肤作痛,甚则皮肉瞷动。胸胁苦满,口苦,头眩,周身乏力,小便赤涩,大便干结。舌绛,苔白腻,脉沉弦。辨为肝郁化火,痰热扰心之证。治以疏肝清热,化痰安神之法。 疏方: 柴胡18g 黄芩10g 半夏20g 栀子10g 陈皮10g 竹茹20g 枳实10g 炙甘草10g 党参10g 龙骨30g 牡蛎30g 生姜8g 天竺黄12g 豆豉10g,大枣12枚 服药七剂,心烦、口苦、头眩症减,每夜能睡四小时,惟觉皮肤热痛,二便少,舌苔白,脉沉,守方再进五剂,烦止寐安,诸症霍然。 本案出现肌肤疼痛、瞤动,乃气火交阻,痰热内扰有动风之象,治疗宗“火郁发之”、“木郁达之”的原则,以疏肝开郁为大法,兼以清火化痰,重镇安神为佐,本方由小柴胡汤、栀子豉汤、温胆汤三方加减而成。用小柴胡汤以疏利肝胆气机,栀子豉汤则清热除烦,温胆汤而化痰安神。 按语:《灵枢·营卫生会》篇云:“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言人之寤寐与营卫气血阴阳的循环转运有关,阳入于阴则寐,阳出于阴则寤。今之治不寐一证,多从心神论治,鲜从气机运转角度考虑。殊不知少阳为营卫气血阴阳运转之枢纽,喜条达恶抑郁,若情志抑郁不遂,使少阳枢机不利,气机不达,则阳不入阴而导致不寐,营卫气血相贯如环,阳入于阴,神敛于心肝则人自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