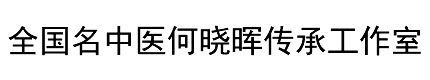摘要:《伤寒杂病论》一书,继承了《黄帝内经》中“人以胃气为本”“土生万物”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守正创新,将调治顾护脾胃的思想贯穿于治疗疾病的始终,时时不忘顾护脾胃,确认脾胃在疾病发生、发展、转归和预后中重要的纽带作用,并把重视脾胃的思想扩展到临床治疗的多个环节,开创了脾胃病的辨治原则,同时创制了脾胃疾病的经典方药,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张仲景;脾胃理论;《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
《黄帝内经》中非常重视脾胃,书中反复阐释脾胃的重要性,《素问·太阴阳明论》和《素问·阳明脉解》专篇论述了脾胃中土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生理上,中央土以灌四滂,脾胃为六气化生之源,滋养诸脏;病理上,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胃亦为痰饮水湿酿生之所,可波及诸脏。《黄帝内经》肇始,历代医家均明脾胃为脏腑重器之理。张仲景将《黄帝内经》中确立的脾胃理论,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实践之中,《伤寒杂病论》中无不体现其对脾胃的重视。详细地归纳总结了各种脾胃病证的临床证候,制定了脾胃病的治疗法则,创制与保存了很多著名的脾胃病方剂,为后世脾胃学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辨证立法顾护脾胃
“胃气”是指脾胃之气,代表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各种生理功能。《灵枢·口问》:“谷入于胃,胃气上注于肺”提出了“胃气”的概念。《黄帝内经》认为人有胃气则昌,人无胃气则亡,如《素问·平人气象论》云:“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伤寒论》全书始终贯穿顾护胃气思想,认为人体的功能与胃气的充沛与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在六经证治中既重视脾胃阳气又重视脾胃阴液,时刻重视顾护胃气。张仲景在扶正祛邪的治疗过程中强调“当和胃气”“胃和则愈”“胃气尚在必愈”“欲得食其病为愈”。仲景从理、法到方、药,处处以脾胃为本,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仲景兼顾祛邪与扶正两端,攻中寓扶,防止胃气耗伤、胃津损伤。
1.1发汗解表,必资汗源
太阳病中,仲景强调发汗过程当中要资养汗源。如太阳中风证“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桂枝汤中桂枝、芍药一散一收,发汗之中寓有敛汗之意,生姜辛散止呕,助桂枝发散风寒,配伍大枣、炙甘草,酸甘化阴,助芍药益阴和营。草、姜、枣三味为调补中州以护胃气,脾胃为营卫生化之本,脾胃安则营卫和,药后以服用热粥,益胃气以助药力,发汗以资汗源。
1.2托邪外出,补中和胃
素体脾胃虚弱,“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病邪入于半表半里,则出现少阳病,少阳病正邪纷争于半表半里之间,若正盛则热势外达,出现发热,邪盛则热郁不发,故恶寒。少阳属胆,胆火内郁则易犯心、胃,出现心烦、喜呕。仲景用小柴胡汤扶正达邪外解,其中扶正主要是补益脾胃,复振中气,方中以大量的健胃补脾药配伍,即人参、大枣、生姜、甘草益气和中,扶正祛邪,使中土健旺,不受木邪之害。
1.3苦寒峻下,保存胃阴
仲景使用峻药攻邪时,以攻邪不伤正为原则,处处顾护脾胃之气。如阳明腑实证以大承气汤攻下燥结,釜底抽薪,仲景时时告诫“得下,余勿服”示人中病即止,不可过伐。在大结胸证中,以大陷胸汤泻热逐水,因其泻下峻猛,易损及脾胃之气,仲景叮嘱“得快利,止后服”提示后世医家中病即止,不可过量,以防损伤胃气。太阳余热未尽热扰胸膈、阳明气分热证,仲景立寒凉清热之法,以栀子豉汤清宣郁热,以白虎汤辛寒清热,在《伤寒论》云“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塘者,不可与服之。”指出临证遇到中焦虚寒、脾虚便溏等症时,当慎用栀子豉汤类苦寒之药,以防苦寒伤胃。在白虎汤中,以粳米、甘草益气调中,做到清而不伤胃气,寒而不致留邪,清热则可保津,使胃中津液得以恢复。
1.4温阳散寒,补土保元
太阴病,以脾阳虚弱、寒湿阻滞为主要病机,仲景提出“当温之”的治疗大法,以理中汤、四逆汤为主方。在温中补虚方中,仲景立小建中汤,合甘温、辛甘、酸甘为一方,具有温养脾胃、健运脾胃、调和营卫之功。少阴病,心肾阴阳气血俱虚,在治疗上仲景以四逆汤扶正回阳救逆为要,共健脾肾之阳。厥阴为病,因肝失条达,木火上炎,脾虚不运,易形成上热下寒、寒热错杂的病机变化,在乌梅丸中,温性药物偏多,其功用在温中健脾,在剂型上以蜜作丸资助胃气,以防药重伤脾胃。
2立脾胃疾病的辨治方药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机升降枢纽,若脾胃为病,则消化、吸收和输布的过程将会出现障碍。《黄帝内经》载:“脾欲甘……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张仲景继承并发挥了《黄帝内经》对脾胃的治疗法则,在《伤寒杂病论》中详细论述了脾胃损伤的诸多病症,创新了脾胃疾病的治则治法与方药。
2.1调脾胃贵在升降
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人体气机的升降始于中焦,若气机升降失和,则脾胃不能升清降浊,运化失司则,脾易寒而胃易热,从而产生寒热错杂,病症上表现为脘腹痞满、肠鸣下利、呕吐、便秘等,正如《黄帝内经》载:“清气在下则生飱泄;浊气在上则生瘨胀。”仲景将《黄帝内经》脾胃升降理论具体运用于脾胃病的施治中,以辛开苦降,降逆调和为法,恢复脾胃升降的生理功能。
仲景设立了以半夏泻心汤为首的诸泻心汤,开创了以辛开苦降法治疗寒热交错、气机痞塞的脾胃病。在半夏泻心汤中,半夏化痰和胃,降逆消痞,使脾升胃降的运动恢复正常。人参、大枣、炙甘草,甘温调补,补脾胃之虚以复其升降之职,全方寒热互用以和其阴阳,苦辛并进以调其升降,补泻兼施以顾其虚实。脾虚气滞证时,仲景以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为主方,也体现了辛开苦降法的临证应用。方中以厚朴之苦,以泄腹满,人参、甘草之甘,补益脾胃,半夏、生姜之辛,以散滞气。以辛开苦降法治疗中焦脾胃气机不畅被后世医家继承和推崇,成了治疗脾胃病的主要方法。
《伤寒论》:“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嗌气不除者,旋覆代赭汤主之。”此证主要病机为胃气虚弱、痰浊内阻,气机不畅导致胃气上逆,也包括客气上逆、肝气犯胃等方面,为虚实夹杂证。仲景立旋覆代赭汤,方中旋覆花能升能降,既能疏肝消痰理气,又能软坚散结消痞,代赭石苦寒,重镇降逆,降胃下浊,二药相伍,既能降上逆之气,可下气消蓄结之痰,有镇肝和胃、降逆化浊之功;半夏与大剂量的生姜配伍,辛温而散、涤痰散饮,解心下痞结,人参、甘草、大枣甘温以补脾胃之虚,诸药合用,使脾胃调和,气机通畅,清阳能升,浊阴可降。
2.2实脾土主用甘温
《黄帝内经》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仲景尊《黄帝内经》旨要认为人体虚证源于人体阳气不足。在《伤寒论》中六经辨证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三阳病多实,三阴病多虚,太阴病以“其脏有寒”为本。若外寒邪伤脾胃则易出现腹满痛、呕吐、泄泻、出血等一系列脾胃病症,仲景予《黄帝内经》治寒之法“寒淫所胜,平以辛热”。若内伤久病或情志所伤,久虚阳气内耗,寒从中生出现的一系列脾胃病症,仲景认为虽有阴阳互损,若见阴虚,不可过于滋腻而折其阳气,当以辛热散寒配以甘补脾阳之法,故仲景补脾胃之法,主用甘温,随证辅以酸收、苦燥、淡渗。
脾胃寒盛,仲景创立了理中汤和建中汤温中散寒,采用大辛大热的干姜、蜀椒等温中抑寒,同时配以甘缓的人参、胶饴、甘草等培土益气温复脾阳,多以理中丸治疗脾虚盛者,以建中汤治疗中寒盛者。在小建中汤证中:“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心中悸而烦”宜用小建中汤,治以甘辛,温中补脾,佐以酸收,养阴而缓肝急。采用大枣、甘草、胶饴之甘以缓中,桂枝、生姜之辛以行营卫,芍药酸收肝气。脾胃阳虚,运化不利,水停饮聚出现痰饮、水肿等症,仲景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为治疗原则,常用甘草、大枣、蜂蜜等甘温之品补脾护脾,苦温之品燥湿化痰,同时加入酸敛之品,与行气、消饮、通阳之品配合使用。主方以苓桂术甘汤辛甘通阳,苦燥淡渗。苓桂术甘汤以桂枝配伍甘草辛甘合化,温通心阳,因脾为湿土,中虚不运,必生寒湿,仲景佐以苦燥的白术燥湿健脾,搭配大剂量的茯苓淡渗而祛除水湿,以温通心阳达到调和脾胃的目的。
仲景在《金匮要略》中以薯蓣丸健脾温阳,以资生化之源,扶正以祛邪。方中干姜、人参、茯苓、白术、山药、大枣皆振脾胃之阳,补中益气。在脾胃出血症中,仲景认为此处出血是由于脾阳不足,统摄无权,以黄土汤温中摄血。方中炒黄土、附子、白术与甘草相伍,亦是治以甘温。此外,若肝脾不和,肝木犯脾土,当泻肝实脾,仲景创吴茱萸汤专治肝寒犯胃浊阴上逆之证,现代研究表明吴茱萸汤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降逆止呕,温中补虚,可达到温养和降肝胃、泄浊通阳的目的。
2.3治胃腑以通为用
胃腑在六经辨证中一般代指阳明。因阳明多气多血,阳气昌盛,所以一旦受邪发病,邪正相争激烈,多表现为大实大热之象。故仲景以“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为阳明病提纲。阳明以实证为主,邪热与肠中糟粕积聚胃肠或邪热与湿邪相结或脾约津液内竭出现腹满痛、绕脐痛、发黄、便秘等胃肠病症,仲景以祛邪为要,以清、下二法以通为用。
热郁胸膈未与痰水互结而影响胃肠,胃气不和,出现“饥不欲食”,仲景以栀子豉汤清宣上焦郁热,栀子豉汤是治疗郁火胃痛的重要方剂。山栀子与豆豉同用,宗“火郁发之”之旨,宣散郁热,上焦得通,胃和则安。在阳明热盛、气壅腹满证中,仲景立白虎汤方解热清胃,若胃热导致气阴两伤,仲景则以竹叶石膏汤清热生津、益气和胃。
仲景亦从承顺腑气,以通为用角度来表达补土思想。胃肠内热,伤津化燥出现心烦、发热、腹胀满、便秘,甚则谵语潮热、腹满痛时,仲景立承气汤清阳明实热,消腹中胀满,通腑燥结。其中调味承气汤泻热和胃;小承气汤通腑泄热,消滞除满;大承气汤峻下燥结,荡涤实热。在《金匮要略》中亦有体现,如因胃肠壅滞,浊气上冲,症见“食已即吐”者,用大黄甘草汤治疗取大黄泄热通腑以降逆若胀重于积,症见“痛而闭”者,治以厚朴三物汤,重用厚朴,行气除满。此外,太阳阳明合病仲景以麻子仁丸润肠通便治疗脾约,方中火麻仁滋脾润肠以顾其本。以大黄牡丹汤泄热逐瘀法治疗肠痈,在治疗疫毒痢疾时仲景以白头翁汤解毒清肠,寒结成实者,治以大黄附子汤。
2.4肝脾同治
《素问·保命全形论》载:“土得木而达。”王冰认为“达”就是“通”,即疏通的意思,即肝木起到疏达脾土的作用,肝的疏泄功能是保证和促进脾胃正常运化水谷的重要条件。肝的疏泄作用影响着脾胃的升清降浊和运化,肝脾功能失和以肝失疏泄、脾失健运为核心病机,影响中焦气机,气机不畅而五脏均受影响,致人失安和。仲景临证时非常重视肝脾二脏,《金匮要略》首条即开宗明义提出“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仲景认为肝实可及脾,肝虚亦可及脾,在治疗上无论肝脾一脏病或两脏皆病,均需注意肝脾同调,多采取泻肝实脾,或培土荣木之法。正如仲景所云“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
小柴胡汤证亦体现仲景治肝为主而兼顾脾胃。方中柴胡气质轻清,味苦微寒,疏解少阳郁滞,黄芩苦寒味重,清少阳郁热,柴芩二药合用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半夏、生姜调和胃气,降逆止呕,人参、炙甘草、大枣益气和中,扶正祛邪,使中土健旺以御木克。全方肝郁得疏,外邪得解,中脾得实。少阴病,四逆散证亦是如此。由于肝失疏泄,木横侮土,出现腹痛、泄利后重,以柴胡疏肝解郁,积实行气散结,芍药调和肝脾,则肝气得疏,脾气得运。
3煎服药物,顾护脾胃
《伤寒论》不仅理法方药具备,而且重视药物的煎服方法,对其做详尽的说明,为后世提供学习的典范。仲景在药物的煎法、服法及药后调护中仍处处体现养护胃气。如桂枝汤服法中明确提出服药后“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同时“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药后啜粥不仅助汗源,也包含着温养脾胃之气,以防汗后伤正之意,而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能够增加脾胃的负担,阻碍胃气运行,导致胃气不足,使疾病往里传变,不利外邪祛除。在大黄黄连泻心汤的使用当中,仲景云:“麻沸汤二升渍之,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这里用沸水冲泡而不煎煮,是取药之气达到治疗的目的,同时,又可免苦寒伤中的弊端。在治疗寒实结胸证时,仲景以三物白散温下寒实,涤痰破结,方中巴豆药性峻猛,易伤胃气,仲景在方后注明“以白饮和服,强人半钱匙,羸者减之……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白饮即米汤,用以缓和药之偏性,保全患者胃气,用热粥或冷粥调节,其目的是借水谷以保胃气、存津液。在十枣汤的使用过程当中仲景亦是时刻顾护脾胃,用大造10枚煎汤,取汁送服。大枣之甘补脾胃扶助正气,并缓和诸药毒性,药后“得快下后,糜粥自养”强调了中病即止,并借糜粥以养正气,使邪去而正不伤。
4小结
《黄帝内经》肇始,历代医家均明脾胃为脏腑重器之理,仲景继承《黄帝内经》的脾胃理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特别强调保护胃气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辨证方法还是遣方用药,《伤寒论》中处处体现出仲景对于顾护胃气的重视。顾护胃气之法,或以升清降浊、燥湿相济;或以温扶阳气、补土保元;或以辛开苦降、调脾和胃;或以通腑泄热、化瘀扶正;亦或以气血同治、温清相宜。同时,在药物剂量、煎服方法、归经选择、服药禁忌以及瘥后调摄方面皆有涉及。综上所述,仲景继承《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并且结合个人的临床经验,将《黄帝内经》中“人以胃气为本”“土生万物”的理论从实际中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对后世补土派的创立也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